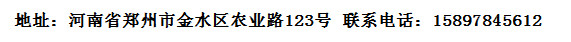身陷抑郁症深渊苦苦挣扎,伪造谎言推开她,
我很爱她。爱到言语具是苍白。但我正在将她推离。用刺耳的话语和刻意伪造的谎言将她亲手推离。尽管我知道这是在刚长出新肉的裂口上补一刀,任重新溃烂的痛苦沿着肋骨往胸腔爬,像一丛放肆的野火继续灼烧,但这种苦涩的温度并不能融化我皮肤上的冰渣。尽管我爱她。我自遇见她起便知道她是一个明亮的人,尽管那时她尚存阴暗面,但她没有糟糕的童年创伤和记忆断层。她的生活环境也是明亮的,包括她的优秀,那是一种让人俯首称臣的优秀。我用了多年去笨拙地追逐她,欲以残存的温度照亮她,并承受着由她加深的抑郁。.4.4,我将四年的痛楚付诸文字,我至今还记得那个人潮喧嚷的午后,她抱着扫帚倚在走廊一角看着我的信,她抬眼的须臾,我明白心上亘久沉默的冻土开始松动。医院窗外的木棉和红枫,随着季节更迭交替燃烧着。灼目的明红色,像我苍白的皮肤上滚落的血珠,又似她的心脏,突突地跃动着,那热度烫得我黯淡的眼角滑出一滴泪来。我们的走过的路艰难,曲折,而离奇。我可以毫不避讳地说,曾经的她推动了我病情的加重,可她始终含愧于心,她又是唯一一个足够将我救赎的人。我从未处于深渊之中,我就是望不见底的深渊,是黑洞,是扭曲万物的魔咒,而她,就像射入我生命缝隙里的一束光,将我一切的恶浊、软弱、不堪的阴影,温柔而勇敢地包裹。当年用kindle看文风繁冗又时不时蹦出个法文单词的《洛丽塔》,我至今记着亨伯特的一句话:“我爱你,我是个怪物,但我爱你。”我真的就是一个怪物。但我依旧这样炽烈的眷恋她的光芒,她有趣而独特的灵魂,时沉静时热闹的性格,认真教我物理时的专注,不知从何下手但奋力对我好时的耿直和笨拙,唱民谣时温柔的尾音。我就像看见一个完整的春季,明媚而鲜活,颤抖的光线跌落在封存的冰河之上,晕开一小片悸动的水渍。我耗尽窒息前的几丝氧气去爱她,无尽欢愉。可就在前几天袒露了我的过往后,我蓦地发觉了我究竟是何种模样。我疯狂挣扎于镣铐中可我无法摆脱,我逃避那些封存的过往和伤疤可它们依旧狰狞地嘲讽我,我流血的悲哀依旧泛滥成灾,在她道过晚安后侵蚀我的理智,我被疾病蛀蚀的骨骼以剧痛提醒我我还在苟且活着。我还是那个被抑郁与红斑狼疮带来的痛苦腐蚀的人,浑身长满霉斑,却极力将自己的不堪呕出让她看,像乞丐一样渴求她的在意与可怜,剖解着自己可憎的悲哀与无用的懦弱,祈求她停留。我不敢看我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在没有天光的阴影里堕落,在充斥盐分的海潮中溺毙,任傍晚的暴雨剥离我稀薄的热度。我能发觉我还是那个无可救药的自己,我能发觉黑暗还是一点一点攀缘于我的皮肤,我最恐惧的事还是在不可遏制地发生,那些蔓延的阴影,想将我完全吞没。可她靠近了。她走进我的生命。我狂喜而狂悲,我知道我等到了自己的光,可更理智的东西告诉我,我会弄脏她的,我不应该将她吸引入我的深渊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私。我本该一个人闭锁地过完一生,而她,是夏日绚丽的日光,值得和其他光线交汇,可我剧烈的渴求让她转向了我,她向我一笑,我只知道有泪水在我的眼眶打转。昨晚我开始审视自己,我到底值不值得这份感情。我知道自己害怕知道这个答案。我只能用那些刺耳的语言来制造隔膜,我知道她讨厌欺骗,所以我极力把暴露出的一切都说成假象,我把自己往最不堪的方向塑造,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失望。我的泪水在屏幕上泛滥,我颤抖地打不出字来,我看着那些从我嘴中说出的冷酷轻佻的话,就像亲手拿刀捅入下腹。白天残存的骨痛还在折磨我,我咬着枕巾痛哭,她一直没有回复,那久久不亮起的绿色显示灯将我最后的防线击垮。我一面渴望她的救赎,我又恐惧她的靠近。你不要再走近了,你不要再对我好了,我是个糟糕的怪物啊。我在无数个泣不成声的深夜,想起她温柔明亮的眼睛和指尖拂过我发顶的触感,我知道,那是我生命中最动人最明艳的色彩,更凸显着我的苍白与残缺。我彻骨地爱她,所以我害怕她被我的黑暗蒙蔽,害怕将羸弱与仓皇暴露给她看,害怕她爱上一个如此糟糕的自己。我狠下心想将她推离深渊,推离这个身负重伤又自私狭隘的我,可我明知她值得更好的,却又疯狂地奢望她的停留,奢望她的拥抱,奢望有她的生命。她真的是骆闻舟一般好的人,可我远比费总恶浊与不堪。村长在《挪威的森林》里写到:我的爱沉重,污浊,里面带有许多令人不快的东西,比如悲伤,忧愁,自怜,绝望,我的心又这样脆弱不堪,自己总被这些负面情绪打败,好像在一个沼泽里越挣扎越下沉。而我爱你,就是希望你救我。此刻的我,正挣扎在对她彻骨的爱与希望她逃离深渊的矛盾中无法自拔。我不知道我还能狠心多久,我已经无法再隐瞒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