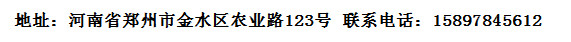疾病
隐喻
年6月30日,大益文学院成功签约12名作家,围绕着今年的签约主题“时代·先锋·未来”,签约作家展开了“疾病与隐喻——小说的未来图景”以及“小说写作新的转折”两个议题的主题研讨,今天的议题是“疾病与隐喻——小说的未来图景”,谈到“先锋”“未来”议题,大益文学院院长陈鹏当仁不让地当起了主持人,各位作家才思泉涌、踊跃发言。于是,便有了这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
▲主持人:陈鹏
▲参与作家:宁肯、樊健军、马拉、
曹明霞、吴文君、陆源、
余静如、周恺、陈小手、奈洛
陈鹏
新年开局一场大疫成了世界灾难,不断攀升的感染人数,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这样的情形在人类的历史上不算少见,鼠疫的三次世界大流行、二十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年非典等等,在这样的巨大灾难过去,也诞生了像《十日谈》《鼠疫》《黑死病》等等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再展开一点说,“疾病”也包含了人类个体的疾病,人类社会发展的弊病,人类发展史的大小灾难,很多优秀作家都用“隐喻”笔法写过此类事件,我们引用了苏珊·桑塔格的书名,但这本书很好地关照了我们当下的世界。各位作家怎么理解“疾病与隐喻”这个主题?
我对“疾病与隐喻”缺乏研究,也从来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但这并不说明我的写作中不涉及这个问题,事实上,从“疾病与隐喻”这个角度思考我自己的创作,会发现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于我的创作中,它几乎是无意识的,天然的存在。在我的五部长篇小说创作中至少有三部涉及到疾病问题,疾病在作品中占有核心位置。比如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沉默之门》中涉到精神病以及精神病院,主角李慢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时代急剧转折中,精神遇到重大挫折,虽然时间并没中止,生活仍在迫切向前,但李慢的精神却像时针一样停止了,最后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毫无疑问,李慢的精神病以及他所住进的精神病院是一代人的隐喻与一个时代的隐喻。
宁肯
提到“疾病”这个词,如果让我联想看过的小说,我最先想到的是加缪的《鼠疫》,鲁迅的《药》,然后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等等,前面两篇多少直接与疾病这个元素相关,后二者并没有,但是心理、生理、行为上不同于常人的表现也常常让人联想到疾病。疾病在文学上可以是一个很宽泛的词,也许正是如此,它也提供很多隐喻和阐释的空间。
余静如
这个议题不可避免的要说到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部分的《铁皮鼓》,甚至《伤心咖啡馆之歌》。再延伸一下,我们可能还会说到写下《好人难寻》《智血》《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的弗兰纳里·奥康纳。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关键词:疾病。至于隐喻,我们在《失明症漫记》中可以获得更为强大的证词。对奥康纳来说,疾病不是隐喻,而是具体的现实。年,奥康纳26岁,她在亚医院确诊弥漫性红斑狼疮,余生她一直被这种难缠的疾病所困扰。这位可怜的女作家,39岁死于红斑狼疮。疾病作为奥康纳的现实,进入小说之中却成了隐喻,她小说中的极端和对人性的不信任,和身体的疾病存在直接的关联,肉体有效地作用于文学。
马拉
我觉得用“隐喻”来表达这次疫情,是有些问题的。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不是从桑塔格那儿来的?我没看过那本书,但疫情期间这两个词铺天盖地,也看了些只言片语,“隐喻”两头通常都是两个派生出的概念,比如用“蛇”来隐喻“性”,“蛇”指的并非真的蛇,在桑塔格的表述里也是,“疾病”并非真的“疾病”,而是派生出的,在“政治”层面,在“关系”层面的意义,它指向的是隐喻后面的那个词。
周恺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处于一种暴躁而伤心的境地,来源于新闻和家庭,铺天盖地的新闻让人无法冷静下来,而家庭的热闹也打乱了节奏,可以说,有两个多月算是荒废了,但也不是没有好处,至少脑子是思考的。也静下心读了《瘟疫年纪事》、《鼠疫》等有关“疾病”主题的小说,我觉得像《瘟疫年纪事》、《鼠疫》这样冷静客观又体现作家高超能力的小说很不好写,记录群体的事件都不好写。
奈洛
疾病与文学一直有着无法剥离的关系,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疾病,不知道有哪些没被作家描述过——相信我在小说里医院里看到的病人更多一点。在现代文学尤其是先锋文学中,文学成为对疾病的另一种拯救,而隐喻则是对拯救的过程拯救的意义所作的阐释。
吴文君
新年以来,我们经历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场猝不及防的病毒,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更有心灵上的焦虑和恐惧。我们为那些逝去的灵魂而难过,而悲伤。这不只是某一个人的灾难,更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灾难。这值得我们认真去反思我们人类的种种行为。这段时间,有不少人在阅读《鼠疫》或《失明症漫记》,也有不少作家创作了或正在创作聚焦疫情的作品。但我暂时还开始不了,我的内心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平静状态。或许以后我会创作类似的作品,那也是在经过沉淀和反思之后。
樊健军
我的理解是在疾病的书写中如何看出现实生活中一些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子,并挖掘出一些闪烁光芒的东西。谈及当下的疫情,我最先想到的是加缪的《鼠疫》,加缪用直接而又深入的语言记录了鼠疫之下的种种世相,这里面的种种让我们很容易便能在新冠肺炎发生初期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关于社会和人心等诸多方面对应的影子。加缪能做到这点,我觉得绝对跟他长久深入的思考和理性全面的剖析分不开,正因为此,他才能借由疾病写出一种“共相”的隐喻。
陈小手
好像是马尔克斯说,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得住的日子。年无疑是个难忘的年头,对所有人来说,它注定要载入记忆。瘟疫打乱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迟滞了大家的脚步。世界安静下来,在安静中,又蕴育着狰狞的风暴。
曹明霞
瘟疫的爆发,潮流的改道,会否让一群人所有改变?我相信生活方式多多少少可以改变,但思维方式,殊难改变,甚至死也不会改变。我们是如此顽固的族类,文人又是这顽固族类之中尤其顽固者。但不在精神层面上谈论改变而空议未来图景,只好陷入“前浪后浪”之类的无效争持。实际上,若无特殊际遇,大部分人六七岁就开始步向衰老了。我们之所以有待于将来,之所以说后生可畏,是因为总有一些人处于正态分布曲线的两端,有幸成为或不幸沦为少数,是有幸还是不幸,端看这少数派分子的思想,改变之妙,存乎一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谈未来图景,才可以谈小说的未来图景。
陆源
各位都谈到了对“疾病与隐喻”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涉?
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疾病“几乎都不仅是局限于它的字面意思,它承载许多功能,比如检验人心与社会,比如释放或约束人性。在我初期的写作阶段里,我非常喜欢探寻一些看起来“非正常”的人,比如我的小说《游戏》中的人物陆奇,一个脑子里有狗毛的孩子。比如《安娜表哥》中的安娜和表哥,因为家族中出现精神病的遗传而影响着正常人对他们的看法。我热衷于探索和虚构他们的生活,因为我认为看似不合理的一切背后都有其逻辑,而当我费尽心思去寻找背后的逻辑时,总是有收获的。虽然在我的小说中,这些主人公都曾被周围的人叫做“精神病”,但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读者并不会这样简单地认识他们。在我现阶段的写作过程中,我又倾向于在看起来寻常的人身上发掘他们与旁人不同的思想、逻辑、行为。
余静如
“隐喻”放在这次疫情当中,我就觉得不太恰当,对当下的我们而言,“疾病”就是实实在在的“疾病”,它不指向任何的派生出来的概念,它是往回溯的,溯回到原始的状态,它不指向任何的隐喻,它指向的就是纯粹的原始的恐惧。
周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症候与投射》,谈到症候与写作的关系,我提出一作家清醒地认识到了解自己到的症候对写作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因为只有作家认识了自我的症候,进而才能培育、发展和丰富自我的症候,才能围绕自己的“根”性症候创作,进而也才能更好地投射自我的症候。
宁肯
艾滋病,阿尔茨海默症,癌症,种类繁多的精神疾病:抑郁,躁狂,或自我冲突,不仅困扰着作家笔下的人物,也困扰着作家本身。很难想象,普鲁斯特如果不是因为哮喘长年闭门不出,是不是还能写出两大卷《追寻逝去的时光》;如果三岛由纪夫不是绝意剖腹自杀,找来介错人为他砍下头颅,是不是还会在死之前留下厚厚四本《丰饶之海》。早上,一位画画的朋友读了我的短篇小说《幽暗》,写